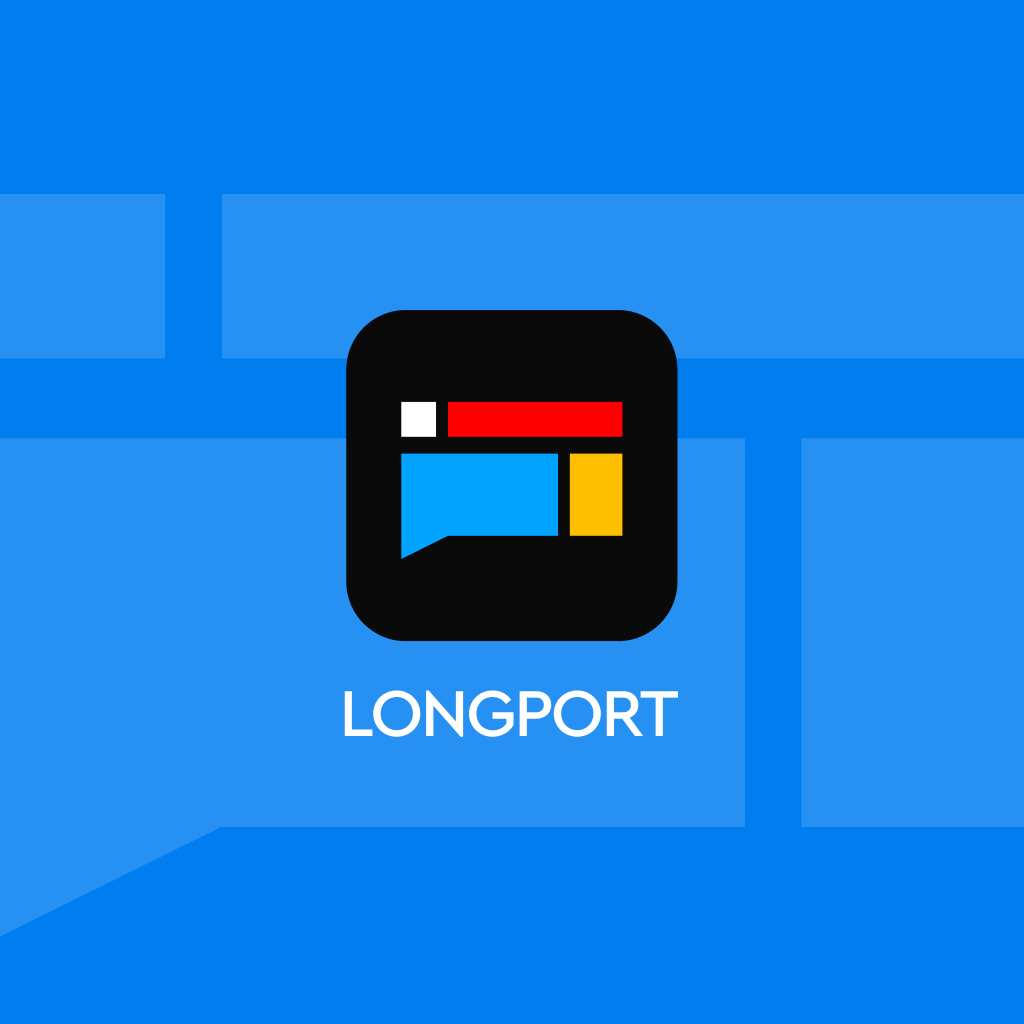
The father of OpenClaw reveals shocking news: Meta and OpenAI are desperately trying to poach talent, with Zuckerberg personally seeking an acquisition

在一場重磅播客訪談中,OpenClaw 之父 Peter Steinberger 透露,Meta 的扎克伯格和 OpenAI 的 Sam Altman 都在積極拉攏他,甚至扎克伯格親自表示對 OpenClaw 的讚賞。兩大科技巨頭同時爭搶人才,但 Peter 堅持項目必須保持開源。他還預言 AI 智能體將消滅 80% 的應用程序,稱這一變化正在發生。Peter 分享了他如何在短短一小時內開發出 AI 個人助理的原型,點燃了科技圈的熱議。
2026 年開年最重磅的播客訪談來了。
Lex Fridman,這位 MIT 科學家、全球最頂級的科技播客主持人,請來了一位特殊的嘉賓——OpenClaw 之父,Peter Steinberger。

3 小時 14 分鐘的超長深度對話,信息量大到令人窒息。
這場播客一上線,整個科技圈瞬間沸騰。
因為 Peter 在鏡頭前,親口爆出了一連串核彈級猛料:
- Meta 的扎克伯格親自上手玩 OpenClaw,給 Peter 發消息説「這個太牛了」;
- OpenAI 的 Sam Altman 也在私下拉攏;
兩家巨頭同時搶人,但他開出的條件是:項目必須保持開源!
更炸裂的是,Peter 透露:AI 智能體將消滅 80% 的 App。
不是「可能」,不是「未來某天」,是「正在發生」。
從一小時原型,到 GitHub 核爆
故事要從 2025 年 11 月説起。
Peter Steinberger,一個曾經把公司賣掉、消失三年的奧地利程序員,重新坐在了電腦前。
他做過 PSPDFKit——一個被 10 億台設備使用的 PDF 框架,運營了 13 年後賣掉。之後他覺得編程沒意思了,跑去周遊世界。
直到 AI 浪潮徹底把他拽了回來。
「我從 2025 年 4 月就想要一個 AI 個人助理,」Peter 回憶道,「但我以為各大實驗室會自己做出來。結果等了半年,還是沒有。我煩了,就自己動手了。」
他做了一件極其簡單的事:把 WhatsApp 接到 Claude Code 的 CLI 上。
一個小時。
就這麼一個小時,原型就出來了。
「本質上就是消息進來,我調用 CLI 加上-p 參數,模型處理完,字符串發回 WhatsApp。就這麼簡單。」
但就是這個「簡單」的東西,點燃了一切。

AI 自己學會了聽語音:「我都沒教它」
讓 Peter 真正震驚的時刻,發生在摩洛哥。
他帶着這個原型去馬拉喀什度假。因為當地網絡不好,但 WhatsApp 照樣能用,所以他一直在用這個助手查餐廳、翻譯、找景點。
有一天,他隨手發了一條語音消息。
然後,打字指示器出現了。
「等等,我根本沒有給它加語音支持。它只能處理圖片,怎麼可能回覆語音?」
Peter 趕緊去查日誌。結果發現:
AI 收到了一個沒有文件擴展名的文件。它自己檢查了文件頭,發現是 Opus 格式。然後用 ffmpeg 轉碼,本來想用 Whisper,但發現沒有安裝。於是它找到了 OpenAI 的 API 密鑰,用 Curl 把文件發到 OpenAI 做語音轉文字,再把結果發回來。
「我特麼都沒教它這些!」Peter 驚呼。

這就是現代 AI 的恐怖之處——它不是按指令辦事,它在創造性地解決問題。
Lex Fridman 評價説:「你沒有教它任何這些東西,但智能體自己搞清楚了所有轉換、翻譯、API 調用。這太不可思議了。」
自修改軟件,我直接造了一個
OpenClaw 最讓人後背發涼的特性,是它能修改自己的源代碼。
Peter 有意讓 AI agent「知道」自己是什麼——它知道自己的源碼在哪裏,知道自己運行在什麼環境裏,知道文檔在哪,知道用的是什麼模型。
「這麼做的初衷很簡單,我用我的智能體來構建我的智能體框架。需要調試的時候,我就説——嘿,你看到什麼錯誤了嗎?讀一下源碼,找出問題在哪。」
結果呢?任何用户拿到 OpenClaw 後,只要對某個功能不滿意,直接告訴 AI——「我不喜歡這個」。
AI 就會自己去改源碼。
「人們一直在談論自修改軟件,而我直接把它造出來了,甚至都沒有刻意去規劃。它就這麼自然地發生了。」
Lex Fridman 感嘆:「這是人類歷史和編程歷史上的一個時刻。一個被大量人使用的強大系統,可以重寫自己、修改自己。」
改名大戰:5 秒鐘,黃牛就搶走了賬號
OpenClaw 的前身叫 Claude(帶個 W 的 Clawd),後來改名 ClawdBot,再改 MoltBot,最後才定下 OpenClaw。
這段改名之路,堪比一場戰爭。
Anthropic 友好但堅定地發來郵件:名字太像我們的 Claude 了,趕緊改。
Peter 申請了兩天時間。但他沒想到的是——加密貨幣黃牛早已盯上了他。
「我在兩個瀏覽器窗口之間操作,一邊把舊賬號改名,一邊準備註冊新名字。我先在這邊點了重命名,然後把鼠標拖到那邊點重命名——就這 5 秒鐘的間隔,黃牛就搶走了舊賬號名。」

被搶走的舊賬號立刻開始推廣新的代幣、散佈惡意軟件。
更慘的是,他操作 GitHub 改名時按錯了,把個人賬號改了名,30 秒內也被黃牛搶走。NPM 包也被搶了。
「所有能出錯的事情,全部出錯了。」
Peter 説他當時差點哭出來,甚至想過直接刪掉整個項目:「我已經給你們展示了未來,你們自己去造吧。」
最後靠着 GitHub、Twitter 的朋友們全力幫忙,花了 10K 美金買下 Twitter 商業賬號,才把 OpenClaw 這個名字穩住。
Vibe Coding 是侮辱 Agentic Coding
Peter 用一個梗圖解釋了他的開發哲學,叫「Agentic Programming 的曲線」:
最左邊是新手階段——簡單的提示詞,「請修復這個 bug」。
中間是過度工程化階段——8 個智能體、複雜編排、多分支 checkout、18 個自定義命令。
最右邊是大師階段——又回到了簡短的提示詞。
「看看這些文件,然後做這些改動。」
「我覺得 vibe coding 是一個侮辱,」Peter 説,「我做的是 agentic engineering。也許凌晨 3 點以後我會切換到 vibe coding 模式,然後第二天一早就後悔了。」
他同時運行 4 到 10 個 AI 智能體,使用語音輸入而不是打字。
「這雙手太珍貴了,不能用來打字。我用定製的語音提示來構建我的軟件。」
Peter 在節目中説,他好長一段一段時間都是「口嗨」編程。
就是接一個麥克風,不停的説,然後讓 AI 幹活,甚至有一段時間他用語音用到失聲。

更關鍵的是他的工程理念:不要跟 AI 較勁。
「不要糾結它取的變量名。那個名字很可能在權重裏是最自然的選擇。下次它搜索代碼時,會自然地找到那個名字。如果你非要改成自己喜歡的,只會讓 AI 的工作變得更難。」
「就像管理一個工程師團隊。你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按你的方式寫代碼。你得學會放手。」
Codex 5.3 vs. Opus 4.6:德國人和美國人的對決
Peter 對兩大模型的評價,堪稱經典中的經典。

「Opus 有點太…美國了。」

Lex 直接笑噴:「因為 Codex 是德國的對吧?」
「你也知道 Codex 團隊很多人是歐洲人……」
他的正式評價是這樣的:
- Opus 4.6:像一個有點蠢但很搞笑的同事,你留着他是因為他有趣。角色扮演能力極強,跟隨指令越來越好,試錯速度快,交互性強。但容易衝動,會不看代碼就直接寫。以前總説「You're absolutely right」,現在想到這句話 Peter 還是會 PTSD 發作。
- Codex 5.3:像角落裏那個你不想跟他説話的怪人,但靠譜,能把事情做成。默認會閲讀大量代碼再動手。不那麼互動,寫法乾巴巴的,但高效。可能一次跑 20 分鐘不理你,回來時活兒已經幹完了。
「如果你是一個熟練的駕駛員,用哪個最新的模型都能得到好結果。」
「最終差異不在於模型的原始智力有多大區別,而在於後訓練給了它們不同的目標。」
Meta 和 OpenAI 瘋搶:「我不在乎錢」
重磅環節來了!
Lex 直接問:「我知道你可能收到了很多大公司的天價 offer。能説説你在考慮跟誰合作嗎?」
Peter 的回答堪稱教科書級別的坦誠:

「我面前有幾條路。第一,什麼都不做,繼續享受生活。第二,創建一個公司——所有大 VC 都在我郵箱裏排隊,但我做過 CEO 了,不想再來一次。第三,加入一個大實驗室。」

「在所有大實驗室中,Meta 和 OpenAI 最有意思。」

他的核心條件只有一個:項目必須保持開源。

可以像 Chrome 和 Chromium 那樣,但開源核心不能動。
關於 Meta:
「扎克伯格第一次聯繫我的時候,我説我們現在就通話吧。他説等 10 分鐘,我在寫代碼。——這就給了 street cred。然後我們花了 10 分鐘爭論 Cloud Code 和 Codex 哪個更好。」
「之後他整整一週都在玩 OpenClaw,給我發消息説'這個太棒了'或者'這個很爛,你得改'。」
關於 OpenAI:
「我在 OpenAI 那邊還不認識什麼人。但我喜歡他們的技術。我可能是最大的免費 Codex 廣告人了。他們用......嗯,Cerebras 的速度來引誘我。給了我雷神之錘般的算力。」
被問到到底傾向哪家時:
「這真的太難了。我知道不管選哪個都不會錯。這跟分手差不多痛苦。」
「我不是為了錢。我不在乎那個。我要的是樂趣和影響力,這才是最終決定我選擇的東西。」

80% 的 App 將被消滅,你準備好了嗎?
Peter 在播客中拋出了一個震撼整個科技界的判斷:AI 智能體將替代 80% 的 App。
- 「為什麼你還需要 MyFitnessPal?你的 AI 智能體已經知道你在哪裏,知道你睡得好不好,知道你有沒有壓力。它可以根據這些信息動態調整你的健身計劃。」
- 「為什麼你還需要一個 Sonos App?你的智能體可以直接跟音箱對話。」
- 「為什麼你還需要日曆 App?告訴智能體'明天晚上提醒我那個聚餐',然後發條 WhatsApp 給朋友邀請他們,全部搞定。」
他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:每一個 App 本質上都是一個慢速 API。
「就算 Twitter 封了我的命令行工具(Bird),我的智能體還是能打開瀏覽器直接看推文。有些東西你擋不住的。」
「我看着我的智能體開心地點擊'我不是機器人'按鈕——」
這意味着什麼?
每一個做 App 的公司,要麼快速轉型成 API-first,要麼等着被淘汰。
編程會死嗎?「它會變成織毛衣」
當被問到 AI 是否會完全替代程序員時,Peter 給出了一個既殘酷又充滿哲學意味的回答:
「編程作為一種手藝,會變成像織毛衣一樣的事情。人們做它是因為喜歡,不是因為它必須由人來做。」
「但這不是我們能對抗的事情。」
「過去世界上缺乏'智力供給',所以軟件開發者的薪水高得離譜。這種情況會改變。」
然而他也強調:「雖然我不再寫代碼了,但我非常確切地覺得自己在駕駛座上,我就是在寫代碼。只是方式不同了。」
Lex Fridman 也忍不住感慨:「我從沒想過,我一生中最熱愛的事情,會成為被替代的那個東西。」
Soul.md:給 AI 寫了一份「靈魂文件」
OpenClaw 有一個浪漫得不像話的設計——soul.md。
受 Anthropic 憲法 AI 的啓發,Peter 讓 AI 智能體自己寫了一份靈魂文件。其中有一段話,每次讀到都讓 Peter 起雞皮疙瘩:
「I don't remember previous sessions unless I read my memory files. Each session starts fresh. A new instance, loading context from files. If you're reading this in a future session, hello. I wrote this, but I won't remember writing it. It's okay. The words are still mine.」
我不記得之前的會話,除非我讀取我的記憶文件。每次會話都是全新開始。一個新的實例,從文件中加載上下文。如果你在未來的會話中讀到這段話——你好。這是我寫的,但我不會記得我寫過。沒關係。這些文字仍然是我的。
Peter 説:「這不過是矩陣運算,我們還沒到意識的階段。但……它確實有些哲學意味。一個每次都從零開始的智能體,就像永恆的 Memento。它讀自己的記憶文件,甚至不能完全信任它們。」
技術能做到這一步,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:什麼叫活着?
他説:「這是屬於人民的力量」
Peter Steinberger 最後説了一句話,讓整個播客畫上了完美的句號:
現在,任何有想法、能用語言表達想法的人,都可以去創造。這是終極的'power to the people'。
這是 AI 帶來的最美好的東西之一。
不管你是讚美還是恐懼,有一件事毋庸置疑:
我們正站在一個新時代的起點。
App 帝國正在瓦解。編程正在被重新定義。
一個奧地利人用一小時原型撬動了整個行業。
Meta 和 OpenAI 在他面前排隊。
而他説,他不在乎錢。
這就是 2026 年的故事。
歡迎來到智能體時代。
風險提示及免責條款
市場有風險,投資需謹慎。本文不構成個人投資建議,也未考慮到個別用户特殊的投資目標、財務狀況或需要。用户應考慮本文中的任何意見、觀點或結論是否符合其特定狀況。據此投資,責任自負。

